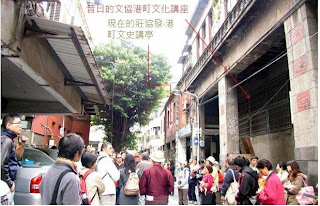|
| 「台灣放鬆鬆」書系第一本《正港台灣人》封面、封底。 |
﹝總策畫序﹞寫於2000年
閱讀歷史,會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嗎?
了解歷史人物,會是一種困難的事情嗎?
放輕鬆!請靠近一點,翻一翻這套書;你會發現歷史並不生澀,歷史也絕不難懂,歷史更不是「遙不可及」的事。
你會覺得歷史人物絕不是「神主牌」,更不是不食人間煙火,何況你所要貼近的是台灣人物,你所要明瞭的是台灣歷史。
沒有錯,就從這時候開始,讓我們走進時光隧道,讓我們回顧歷史長廊。
學習歷史,最快的入門方法是閱讀傳記,正如史學家羅斯(A.L.Rowse)所說的一句話:「閱讀傳記是可以學到許多歷史的最便捷方法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