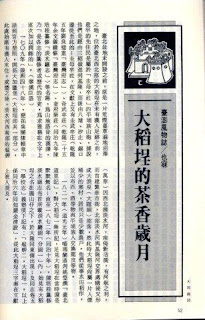「讀其書,不知其人,可乎?」古早人的話,我改為「知其人,不讀其書,可乎?」知我之人,成千累萬,或讀我的著作、或聽我的演講、或參加我的導覽,希望您們捧個人情,湊個熱鬧,閱讀我的新作《活!該如此──莊永明七十自述》(遠流出版公司)。
〈自序〉暢所欲言又止
不該出而出的這本書,決定成書,原因是自己平凡的生命史,所見、所聞、所感的人、事、物,不少是歷史的見證。
浪費「紙」源,知其不可為而為之,畢竟以三年半的時間,在《文訊》雜誌刊載的專欄「心路,筆痕.書影」,如果未能結集,殊為可惜,乃決定以《活!該如此」做為回憶錄的書名。
兩句話,可以道出心情故事:
同歷史獨白有話
與現實對話無語


.jpg)